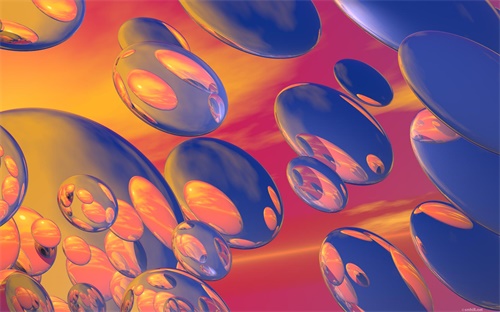历朝历代都有外戚专政,为何到了明朝便销声匿迹了呢?

外戚专权是我国封建历史上一种常见的现象,许多王朝灭亡的原因都有外戚专权的影子,强如西汉就是被外戚王莽篡位而亡。但到了明朝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外戚几乎没有存在感。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困扰多个封建王朝多年的外戚问题在明朝得到较好的解决呢?明代后妃普遍出身较低朱元璋在位时期,苦心孤诣为自己的子孙后代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祖训。
为的就是防范有人能夺走朱家的江山。因此对于后宫干政和外戚专权这两条朱元璋都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明太祖朱元璋曾经令人编撰了一部《皇明祖训》,也即明朝皇族的家法。里面关于后宫的《内令》一章中就明确有两条关于防止后宫干政和外戚专权的规定:凡皇后止许内治宫中诸等妇女人,宫门外一应事务,毋得干预。凡天子及亲王、後、妃、宫人等,必须选择良家子女,以礼聘娶,不拘处所;勿受大臣进送,恐有奸计。
但是娼妓不许狎近。这两条很明确的规定了一是明朝后妃不得干政;二是后妃必须从身份较低的家庭选择。其实后妃不得干政这条并非明朝首创,其他朝代也曾经有过。但是如明朝那么严厉还是比较罕见,尤其是从身份较低的家庭选择后妃的做法比较特殊。我们从明朝的历代皇后来看,也可以印证这一家法祖训。除了明成祖朱棣的徐皇后是魏国公徐达之女外,其他皇后大都出身中下级官吏或监生家庭。
后妃的家族出身低就相对难以形成较强的政治势力和团体。因此明朝首先在源头上就预防了外戚势力形成权力集团。科举制使外戚势力缺乏生存空间外戚势力与宦官专权都是依附于皇权而存在的政治势力,如果没有与皇帝的姻亲关系或者皇帝的宠信外戚势力很难形成政治影响力。在我国封建社会初期,官员选拔制度尚不完善,主要采用察举制,也即依靠推荐和考察。
这种制度很容易形成裙带和宗族势力,而且选才面很窄。这就必然导致皇帝可以依靠和信赖的政治势力很有限。出于维护自身皇权稳固的角度出发,必然会从最亲近和最信任的群体加以重用,这就是宦官和外戚容易上位成为重要政治势力的原因。而从隋唐时期开始采用科举制来选拔官员之后,封建社会政治体制中就逐步形成了一支通过科举上来的文官集团。
这个集团没有世家大族的背景,他们的权力也只能依靠皇帝的信任,而且他们所受到的儒家教育也是以忠君为前提,所以也就成为皇帝可以信任和依赖的一支重要政治势力。以明朝为例,在宦官势力强大到可以威胁皇权的时,明朝的文官集团就是维护皇权最好政治势力。但是文官集团的强大又让皇帝感到无法抗衡和驾驭,于是又抬出身边的宦官来压制文官集团,明朝中后期的历史大体上就是这两支势力的抗衡。
刚才已经提到明朝的后妃出身都不高,虽然外戚大都会被封为伯爵或者侯爵这样的高等级爵位,但是没有通过科举入仕,同时因为明朝抑制外戚出任实职因此就很难在文官集团和宦官集团之外形成第三股政治势力。综上,明朝没有出现外戚专权的主要原因一是明初朱元璋制定了严格的祖训家法,对后妃干政和外戚专权进行了预防。特别是严格把控后妃的家族出身,避免外戚势力乘势坐大。
明朝有一种“朝天女”,世袭官职,享尽荣华,为何却闻者色变?

洪武三十一年五月,70岁的朱元璋躺在病榻上连喘粗气的力气都没了。如花似玉的嫔妃们平时难得龙宠,这会儿奉命轮流御前侍疾,这一天伺候老朱的是翁妃和李淑妃。翁妃是蒙古弘吉剌部人,六年前老朱夜读《元氏》,读到弘吉剌部强盛往事时,忍不住问侍臣:“弘吉剌部还有后人吗?”弘吉剌部是蒙古草原上五大部落之一,以盛产美女著称,蒙古贵族都以娶到弘吉剌女子为荣,成吉思汗的母亲和妻子都是弘吉剌美女。
侍臣心领神会,不久就带来南海卫正千户瓮氏14岁的姑娘。从那时起翁姑娘入宫,伺候老朱六年,只是没有生下一儿半女。翁妃身上的香气阵阵,飘入老朱的鼻孔。沉睡了很久的老朱醒来,定定地看了她好一会儿,嗓子里呜噜呜噜地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身边人辨析良久才听清:“能久侍朕乎?”意思是你们能长久地侍奉我吗?这话问的,纵然心里一万个不愿意也不敢说呐!于是二人跪倒呼万岁,意思是妾等伺候陛下那是无上光荣,俺们愿意天天伺候您。
老朱一脸冷笑:真蠢,都听不懂话外之音,朕的意思是你们愿不愿意到地下,永远伺候朕?翁妃、李淑妃愣了半晌才明白了这个“久”字是什么意思,顿时吓得浑身筛糠,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老朱一撂脸:赐白练,给朕殉葬吧!估计一旁的皇太孙朱允炆都被搞傻了:老头病糊涂啦?人家汉武帝立子去母,这两位也没儿子啊,杀她们干嘛呢?这个故事记载于査继佐的《罪惟录》,没有交代题干中的“朝天女”跟这个故事有什么关联,《明史·后妃传》交代了:“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
建文、永乐时,相继优恤。如张凤、李衡、赵福、张璧、汪宾诸家,皆世袭锦衣卫千百户,人谓之‘太祖朝天女户’。历成祖、仁、宣二宗皆然。”原来,朱元璋让翁妃、李淑妃殉葬跟政治无关,纯粹是“个人爱好”,而且殉葬的远不止瓮、李二人。这些被殉葬的女子就是“朝天女”,她们的家属就被称为“朝天女户”,会享受优待政策,这个习俗后来成了惯例。
殉葬这个陋习,作为早期贵族葬礼的“规定动作”,早在春秋战国就饱受争议,因此慢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朱元璋却恢复了这个残忍的制度。那些饱读诗书的文人士大夫也知道这么做容易挨雷劈,所以在史料中尽量掩盖,导致很多细节不得而知,我们从零碎的资料中整理出以下几个细节。什么人能有资格做“朝天女”?有一种说法是,“朝天女”是那些没有生育的嫔妃,但这个说法未必准确。
以朱元璋为例,给他殉葬的女子有46位(此数字有争议,有十几个,38个等多种说法),其中宝庆公主的生母应该就是“朝天女”。朱元璋驾崩时,宝庆公主才3岁,是老朱最小的一个孩子。民间传说其生母张美人因此被特赦免于殉葬,但在《文皇帝实录》中却记载说:“主,太祖皇帝第十六女也,生而太祖崩,母张氏亦卒。”意思是老朱驾崩时张美人也死了,怎么死的?没交代。
如此巧合,大概率成了“朝天女”!明仁宗朱高煦驾崩后,他的宠妃郭贵妃也成了“朝天女”,但她却生了三个皇子。由此可见,所谓“朝天女都是没生过孩子的嫔妃”之说,是靠不住的。那么,到底“朝天女”的选择标准是什么?谁有决定权呢?从目前史料来看,“朝天女”选择根本就没有标准,所有的嫔妃,甚至宫女都有可能进入“光荣榜”。
只有一个人肯定被排除在外,即皇后。而决定“光荣榜”名单的,正是皇后和太后。“朝天女”能得到什么优待?求生是人的本能,这些青春年华的女子谁不留恋人间?更让她们恐惧的是“朝天女”的死法。所有朝天女梳洗打扮后被集中在一间大殿,横梁上早就悬挂好了一排排白绫,女人们哭作一团,哆哆嗦嗦爬上凳子,在太监们的催促中将白绫套在脖子上。
太监一脚踢开凳子,一条鲜活的生命在痛苦的挣扎中消失。倘若遇上胆小的,或者不愿意配合的,就会有人帮忙,强行帮她升天。据说还有被毒杀,或者被灌水银而死的。但无论哪一种死法,那么多人哭声震天,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姐妹顷刻香消玉殒,谁不胆寒?假如有儿女在人间,那种生离死别岂不是撕心裂肺?唯一让“朝天女”欣慰的是,她们的死会得到三个补偿:一,火线提拔临死前,“朝天女”的等级获得到提拔,甚至坐火箭破格“升职”,同时赏赐一个美谥。
比如宋仁宗的谭昭容晋升顺妃,谥号“恭僖”,明宣宗的何贤妃晋升为贵妃,谥号“端静”。二,配飨祭祀祭祀在古人心目中是头等大事,得不到祭祀的人就是“孤魂野鬼”。有资格与皇帝一起,在祭庙享受祭祀的除了皇后外,还有少数重要的大臣及妃嫔,当然,他们只能叫“配飨”,意思是皇帝与皇后坐主位,他们陪吃。本来没资格“上桌”的女人们,因为“朝天女”的身份获得了配飨资格,身后不愁挨饿了。
三,福荫父兄在现代人眼里,这一点最实惠,可惜跟“朝天女”本人无关。“朝天女”的父亲或兄弟,会获得锦衣卫千户,或者百户的带薪职位,且可以世袭。锦衣卫千户正五品衔,百户正六品衔,不算太低,关键是能世袭。但如果你以为这是个“永久饭票”,那就未免太天真了。古代所谓世袭,很少有超过三代的,朝廷有的是办法给你剥夺了。
因此,所谓的补偿其实不大靠谱,如果女子们能有选择的权利,估计没几个愿意做“朝天女”。明朝谁有资格获得人殉待遇?值得注意的是,明朝不光是皇帝,诸侯王也有获得人殉的资格。比如周王朱有炖,他的王妃巩氏,以及夫人施氏、欧氏、陈氏、张氏、韩氏、李氏,就全部被殉葬了。由于朱家人开了个恶劣的先例,导致民间殉葬之风抬头,但都打上了“自愿”这个遮羞布,舆论也鼓励所谓的“贞洁烈女”给丈夫殉葬。
“朝天女”制度是如何终结的?从朱元璋恢复殉葬制度后,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代宗朱祁钰都用了“朝天女”,五位皇帝的殉葬女一百多人。谁也没想到,宣布废止殉葬制度的居然是大明王朝最没有作为的明英宗朱祁镇。明英宗曾经在土木堡被蒙古人俘虏,又被弟弟囚禁多年,大概是经历了生死劫难,对生命有了反思吧。。
落魄时赵匡胤来投王彦超,王彦超给了十贯钱把他打发走了,后来赵匡胤如何处置他的?

中国古代史上一桩有着“莫欺少年穷”意义的“鸡汤典故”,正是“王彦超给了赵匡胤十贯钱”后汉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是未来的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人生无比灰暗的一年。这位时年二十岁的“开封官二代”,正赶上“后晋”变了“后汉”,亲历了开封的战火浩劫,身为高官的老爹赵弘殷也失了势。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眼看要揭不开锅。
刚结婚没几年的赵匡胤,也就毅然结束了“啃老”生活,一跺脚外出闯荡,誓言要凭自己一身武艺,打拼出一番天地来。可理想很丰满,乱世太骨感。离家后的赵匡胤,闯了好些个地方,无一例外都闯得头破血流。身上的盘缠曾被强盗抢了个精光,流落到长安时,身上就剩了两块冷干粮。后来连干粮都没有了,甚至还跑到寺庙的菜地里偷莴苣吃。
比起野史里那“千里送京娘”的英雄风采来,真是怎一个灰头土脸了得。也正是在尝尽了太多世事辛酸后,没脾气的赵匡胤也想着走捷径——靠父亲从前的“老关系”谋个前程。怀着这坚定信念,他又从北方一路跋涉,来到复州(湖北仙桃)投奔父亲的“老同事”,复州防御使王彦超,满以为能在这位“邻家大叔”麾下有个一官半职。没想到这位“王叔叔”却十分冷淡,只是塞过来十贯铜钱,就把这“赵大侄子”打发走人。
如此一幕,也正如学者顾宏义的评价:“大概王彦超不会料到,当时自己像打发叫花子一样对待的落魄汉(赵匡胤),在十数年后会成为能主宰自己生死的天下第一人。”而放在一些“鸡汤文”里,这位王彦超“大叔”也遭到过不少嘲笑,俨然成了有眼无珠的势利眼。但事实上,这人,没那么简单。虽然与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是“老同事”,但王彦超的战场生涯,显然传奇的多。
十二岁的时候,他就作为后唐将领征战沙场。后晋年间石敬瑭给契丹做“儿皇帝”,割让燕云十六州时,他就是后晋“外交官”桑维翰的随从,等于亲身参与了“交接”。后汉至后周年间,特别是“打发走”赵匡胤后,他又踏上了抗击辽国的战场,多次跟随柴荣痛击契丹精锐,闹哄哄的五代十国时代里,公认的一代良将。而比起战场上的大杀四方来,这位良将更有个出名的品质:厚道。
比如早年跟随后唐名将李继岌作战时,正赶上后唐朝廷政变,昔日位高权重的李继岌,分分钟成了不如鸡的落毛凤凰。李继岌身边的心腹们纷纷叛变跑路,却唯独王彦超不离不弃,一直忠心耿耿跟在李继岌身边,直到李继岌身亡。放在叛变反水甚至“黄袍加身”成习惯的五代十国年间,这厚道,着实异类。带兵风格也是异类,别的“名将”多喜欢纵兵奸淫掳掠,他却治军严格,“所至民安之”。
别人打仗不择手段,宁可尸山血海也要打赢。他却常在战事激烈时叫停,只要能减少伤亡,能劝降敌军就去劝降。这样一个厚道且有原则好军人,怎么偏偏对“大侄子”赵匡胤势利眼?首先一个原因,就得看看赵匡胤当时的境况。别看这是王彦超的“故人之子”,可就算是赵匡胤的老爹赵弘殷,也只是王彦超多年未见的老同事,此时隔着千山万水,突然冒出个“大侄子”跑来求工作,而且这“大侄子”一路颠沛流离,浑身衣衫褴褛,满眼一幅穷困潦倒的模样,还拍胸脯说自己是一代英才,这人,能信?更何况,此时正是中国古代史上乱到糟心的“五代十国”乱世。
北方的五个王朝,总计国祚就才53年,平均每十年就要改朝换代。“五代”里的十五位“九五之尊”,七个是靠篡位政变上台,其中五人的“篡位”,更是以骨肉相残为方式。那个年月里,“部下反大将”甚至“大将反皇帝”,全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放在王彦超这样的“防御使”身上,日常收个部下,真要瞪圆眼睛。突然冒出来的赵匡胤,怎么能信?换句话说,放在那个时代,除了像后来赵匡胤的“老上级”郭威(后周太祖)那样,有着犀利眼光的英雄外,当时那个落魄模样的赵匡胤,走哪都很难有人收。
王彦超看不上赵匡胤?真是很正常。而另一个原因是,“王彦超给赵匡胤十贯钱”这事儿,看上去很势利眼,但放在当时,已经很不错了。五代十国战乱,一个出名的后果,就是严重的“钱荒”。铜钱早已是“久绝铸造”,大量的贵金属被有钱人“藏储私事”。民间老百姓用的,多是铅钱之类的“恶钱”。一枚铜钱在后汉年间,往往能抵百枚铅钱。
如此兵荒马乱的年月,遇上一个多年不见的“落魄故人之子”,王彦超“出手”就给了赵匡胤十贯钱,那真是一笔不小的钱。比比赵匡胤接下来的遭遇,就知道王彦超做得怎样。被王彦超“打发”走后,赵匡胤又投奔了父亲的好友——随州刺史董宗本。论关系,董宗本比王彦超亲的多,也就收留了赵匡胤,可董宗本的儿子董遵诲,却对赵匡胤无比忌恨,逮着由头就各种挤兑,终于气的赵匡胤拂袖而去。
相比之下,关系没那么“亲”的王彦超,做得已是很不错了。在青年赵匡胤这一段尝尽世态炎凉的悲催人生里,王彦超做的,已是非常厚道。所以,对于赵匡胤来说,这一段磨难,他真没当事儿。别说是“塞钱”的王彦超,就算是羞辱过他的董遵诲,后来在皇宫里与他再见,吓得当场就在他面前“伏地请死”。赵匡胤却是哈哈一笑,摆摆手这事儿就过去了。
对董遵诲都如此,对王彦超更如此。一次与王彦超喝酒,喝高了的赵匡胤,也问王彦超那时“何不纳我”。王彦超忙回答说“勺水岂能止神龙耶!”赵匡胤又是哈哈一笑,第二天又“遣中使慰谕”。经历过那个苦难年代的他明白,王彦超能做到那样,真是不容易了。所以相比之下,赵匡胤对那个乱世印象最深的,与其说是自己受的窝囊气,不如说是他在那一番颠沛流离里,亲眼见证的民间苦难。
正是这深刻的苦难记忆,支撑了他在位十七年的坚定信念:力排众议废除了五代时期的大量苛捐杂税,十多年如一日鼓励垦荒,“优待文官”的他,更以酷烈手段,严惩五代时期流毒般的贪暴害民现象。甚至软硬兼施,铲除了唐代以来“藩镇作乱”的土壤。每一个举措,都来自当年的刻骨铭心。而在这样的变革时代里,当年“厚道”的良将王彦超,也是“厚道”依旧。
从“杯酒释兵权”起,他就主动“配合”宋太祖,交出了手中兵权,也因此继续安享高官厚禄。宋太宗年间时,他更主动“知止”,辞掉一切闲职。致仕回家后,晚年更是低调善终。如此作为,也正如北宋学者曾巩的评价:“时以为彦超居富贵能知止足。”比起好些人津津乐道的,乱世里“识人”的眼光来,“势利眼”王彦超的一辈子更证明:眼光可以有差距,但真正的格局,是做一个有原则有良心,识大体顾大局的人。
文章T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