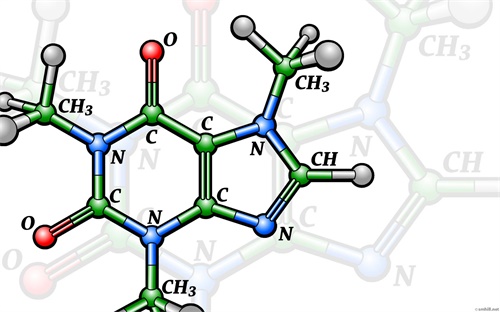小四锅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汗毛全都立起来,他对麻老邪的这个故事最为好奇,尽管他听了不下十遍,但每遍都让他觉得特别过瘾。在听了麻老邪的这个故事后,小四锅妄想着也可以碰见那叫他既害怕又向往的一幕——某天放牛,在一个树林茂密的山沟里,夏虫噪鸣,当他抬起头时,一具眼睛瞪得老大,舌头拉得老长的尸体,随着热风在他眼前荡峳。
尸臭味吸引了一大堆苍蝇围着尸体转。后来有件事让小四锅难以接受,每次妈妈让他去楼上拿鸡蛋或者其他东西时,他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象房梁上会高挂着一具尸体,随着木窗吹进的凉风前后摆动。突然出现的老鼠爬动或者猫的移动都会让他尖叫,全身哆嗦。小四锅很矛盾,到底是应该庆幸自己听到那个故事,还是应该觉得无奈呢。“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
”一个回合终于结束了。小四锅放下酸软的手臂。第一天过去了,第二天过去了,第三天又过去了。突然有一天,小四锅感觉自己已经掌握了电视剧里的“武功秘籍”,空有一身好武艺,但是无法施展。他无聊的端着枪,东瞄瞄西瞄瞄。一会儿瞄着远方的树干,一会儿瞄着荒地里黄牛才拉出的粪便,一会儿瞄着麻老邪那只四个指头的左手,最后他把目标定格在了正在吃草的名叫“包头”的小黄牛身上。
此时他脑海里泛起一阵说不出的兴奋,似乎难以压制。——碰——小四锅偷偷扣动了狗脚(扳机)。空弹。但当他听到撞针的撞击声后,胸膛里的心快从嗓子眼跳出来似的。紧张、却很释然。他有了第一次尝试。麻老邪总是把装有弹药的牛角藏得严严实实。小四锅来回琢磨到底藏哪里,最后都是怏怏而止。他只见麻老邪没事时总拿一块粘着油污的抹布擦枪管,用一张磨得发白的砂纸蹭撞针,但从没看见他放过一枪。
农历六月十五的那天下午,天热得发了狂。太阳像一个倒扣着的火盆子,肆无忌惮地炙烤着山野。一些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地火低低地浮于地表,使人觉得憋气。一点儿风也没有。小四锅看了看灰红的天,看了看在荒地上正在吃草的水牛和黄牛,再看了看荒地边树荫里大张着嘴巴鼾声骤起的麻老邪。山林里的灌木树像病了似的,叶子挂着层热浪在枝上打着卷;枝条一动也懒得动,无精打采地低垂着。
荒地上一个水迹也没有,干巴巴地发着灰光。腾腾的地火飞起老高,跟天上的灰气联接起来,结成一片毒恶的热浪阵,不断烫着小四锅的脸。处处干燥,处处烫手,处处憋闷,整个山林像烧透了的砖窑,使人喘不过气来。土狗趴在地上吐出红舌头,水牛的鼻孔张得特别大。山林寂静,只有牛脖子上套着的铃铛发出使人焦躁的一串单调的叮叮当当。
小四锅蹑手蹑脚地靠近正打呼噜的麻老邪。他一向都不喜欢麻老邪睡觉的样子,嘴巴张开,耷拉着,好像做一个苦梦。他也不喜欢看到麻老邪睡觉时,假牙在嘴里滑得歪七竖八。睡觉时的麻老邪眼皮一直在微微的颤动。小四锅又坐在地上定了定神,他再次用目光在麻老邪的全身上下打量,好像小偷在找寻下手的猎物。“——啊——”麻老邪不时地发出吼声,小四锅还是像触电似的蹿起,弹得老远——尽管他经常说服自己去习惯麻老邪的这种怪吼。
小四锅发现自己已经汗水外溢,从鼻尖滴下,还有少量渗进眼眶里,一阵辣痛。他清楚这是麻老邪在睡梦里习惯性发出的梦魇,可还是乱了手脚。东摸西摸,终于在麻老邪充当腰带的红布条带里找到了装有弹药的牛角。小四锅惊喜且亢奋,脑袋却仿佛一片空白,似乎忘记自己在做什么。战战兢兢地模仿平时里麻老邪往火药枪管里倒入弹珠,再在撞针处擂上火药。
“端稳,端稳。”他在内心深处重复着平时麻老邪教他练习的词语。不知不觉,他又把瞄准的对象锁定为正在吃草的小黄牛“包头”脖子上的那个铃铛。此时,他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给火药枪装上弹药。是为了更好的瞄准嘛?不是,瞄准是不用装上弹药的,他很清楚这一点。既然装上弹药了,为什么不开一枪试试呢?不,“枪响了就得出事。
”……(已省去几千字)小四锅扔掉枪跟在麻老邪身后跑到“包头”身边。只见它口吐白沫,鼻孔喷着粗气,乌黑的一滩血淹死了一大片前来搬运食物的蚂蚁,眼睛睁得像两个松果,死死地瞪着小四锅。对于小黄牛,对于小四锅,突如其来的事故都仿佛是一场噩梦。噩梦终究会醒来,但这一切都作为现实而残酷地存在着。至今小四锅还记得那双眼睛——茫然、可怜、无奈。
文章TAG:弹弹 博士后 蚂蚁 噩梦 奖励